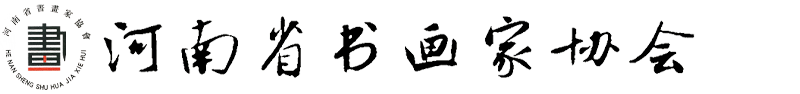中国史诗性审美传统及其意
作为文体的史诗和作为观念的史诗性审美,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经中国学者、作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努力,经历了“史诗性审美在中国”到“中国的史诗性审美”之转变,逐渐形成中国的史诗性审美传统。作为中国社会形态、生存情境的一种编码形式,史诗性审美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中。它以对生活广度、深度、厚度的反映,对民族性格的挖掘及所激发的庄严崇高的审美效果等特质,与中华民族的自我认知、民族身份和民族精神的建构产生深刻关联,并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修辞功能。
呈现丰富文化景观 中国有无史诗,是20世纪初中国学界曾热烈争论的问题。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以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为题材,在不同历史阶段创作出不同形态的史诗性文本。中国的史诗性审美在种类、媒介和受众等方面均呈现出多元化景象。 在现代文学史上,史诗性作品一度成为表征民族国家叙事最受欢迎的叙事体裁,先后涌现出多种史诗模式:茅盾创立的“子夜”模式,巴金、老舍代表的“平民史诗”模式,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开创的“土地史诗”,及叙述革命斗争、反映人民普遍觉醒和抗争的革命史诗。这些史诗性书写,面向中国厚重的历史,将民族精神、民族事件、民族性格等作为描写对象,记录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具有客观性、整体性、全景性、民族性等史诗性长篇小说的基本特征。
史诗性书写成为现代文坛上最富感召力的中心符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保卫延安》《创业史》《红旗谱》等一系列史诗性长篇小说纷纷涌现。这些后来被称为“红色史诗”、社会主义史诗的作品着眼于时代的宏大主题,反映国家经验,唤起人们对社会新制度的认同和对未来的向往,充满理想、浪漫、崇高气息。这些“红色史诗”最终成为特定时代“革命文学的理想形态”。
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上出现了“文化史诗”运动。海子等一大批诗人通过对民族历史和传统的想象创作文化史诗,观照隐含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着力探求华夏民族独立于世界的文化和精神资源,创作出具有“宏大想象”“宏伟叙事”与“深度思辨”的现代东方史诗。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史诗性书写在长篇小说领域占据了重要位置,“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就有不少具有史诗性风格,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等。这一时期的作家在创作理念、手法上不断探索创新,以文化史、人性史、生命史、民间史来进一步丰富史诗性书写,突出国家民族叙事下的个体生存叙事,更为全面地呈现中华民族复杂多样的生存景观。 在影视领域,史诗电影、电视剧为满足人们对于历史感、宏大时空、民族性、英雄性、崇高感等史诗性元素的强烈而持久的审美需求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学、文化文本,使“史诗性”审美拥有了更多受众。近年来,中国影视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史诗性作品,比如从文学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白鹿原》、以生活化视角讲述周恩来总理故事的《海棠依旧》、将民族创业史与个人抗争传奇史融而为一的《闯关东》等。
铸就文学审美理想 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丰富的史诗性文本,我们提出中国史诗性审美传统说。这既能有效概括分散的史诗性审美现象,又可与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说互为补充。这一命题的提出,可将抒情与叙事、诗与史、审美性与思想性有机融合,进一步优化史诗性书写,从而铸就更为完善、丰富的文学理想和审美理想。 20世纪70年代,海外汉学家提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抒情诗的国度,“心与物游”“感物吟志”“以诗写心”的抒情性审美取向是文学主流,对客观世界的描摹和对事件的叙述则在抒情之后,为抒情服务。“抒情传统”说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传统和文化理想,但遮蔽了中国的叙事传统。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跌宕起伏,这已远不是篇幅短小、优雅精美的抒情诗所能充分反映的。闻一多认为,中国文学不能再固守于抒情诗,只有走出抒情、吸纳叙事才可能找到生路;王国维也很早就表示,虽然中国的叙事文学有一定缺陷,但他期望未来的中国文学家在叙事文学方面有所作为。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基本逻辑是从抒情走向史诗,创作现代民族史诗成为创新中国传统文学体裁系统的重点和方向。由此,“史诗性”书写伴随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逐渐发展成一种稳定的审美传统。 当然,抒情性和史诗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抒情传统和史诗传统对于现今的中国文学和文化来说应是二重奏,以抒情性遮蔽史诗性,或以史诗性遮蔽抒情性都是偏颇的。史诗的两端——史,强调真实反映广阔的生活;诗,强调作品的文学性、审美性。真正优秀的史诗性作品追求“有情”与“事功”、“抒情”与“叙事”、小我与大我、形式的艺术性与内容的真实性的结合。努力实现抒情性与史诗性并举,实现诗与史、抒情和叙事的融通,以此审美理想为参照,中国文学和艺术创作才能达到新的高度。